本文为《看历史》三月号“开卷”
2010年12月刊和2011年1月刊《看历史》杂志相继推出溯源历史教科书上地动仪和司南的文章。细细读过,深深感佩科学家们的精神。不论是燕京大学生王振铎、日本学者服部一三,还是中国学者吕彦直、李善邦,皆以一种科学的求真精神,探寻古代科技的运行原理,在古代与现代科技之间矗立一条通道。这种“为真而真”的精神正是科学的真正源头。
然而,出于国家意志和现实需要,这种科学探寻被工具化。于是,把推测当作事实,进而造出一件“实物”,赠予友邦,甚或写在历史教科书中,却不作真实详尽的说明。原本最可资宣扬的科学精神,让位于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爱国教育。余英时先生曾说,近代以来,中国人缺少文化超越性,急功近利、专重物质成就,故而,“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,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,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借”。(余英时:《论文化超越》)
此种功利性不止表现在科学领域,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尤为深重。本刊地动仪复原模型溯源的文章发表后,引发了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回应态度。一种动辄言及是一骗局,地动仪根本无法预测地震,甚而抬高到国民自信轰然倒塌等等;一种把还原历史的努力视作庸俗的求证主义和批判主义,甚至扣上一顶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。这两种态度,各有认识上的深浅,本质上却是一体两面,他们皆是历史实用主义者。
第一种人由某件具体事项的否定,进而上升到抽象否定。因为科学研究与实践有一段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历史,便因此迁怒、否定整个传统。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地动仪?地动仪究竟可不可以验证地震?这些不是不可以探讨的问题,但这些问题终究要靠是专业人士的考证研究。第二种人则视历史传统为传说中金蝉子长老转世的唐僧肉,何时想吃便拿来煮着吃,如此一来,当真就可以功力倍增、长生不老。竟是抬祖宗棺材以壮声势了。似乎一国之尊荣,万民之信心,全赖有无地动仪或地动仪动了没有。第一种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,常见的结果是陷入恶性循环,以暴易暴,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。第二种人则浅薄狂妄,自以为站在最高点,以往历史随手拿来,当锅刷还是鸡毛掸子,全凭一己心情与好恶。
时至今日,我们仍然不能以一种清澈的理性态度,对待以往历史。如果说历史是今日的我们所来自的地方,则她的荣耀,她的耻辱,便都是我们的一部分。全然地接受真相,而不是选择性地放大或摒弃,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。何况历史总是变动不居的,谁也写不出一个最后的定本。历史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民主化,于是才有所谓公共史学的出现。
历史自有她的现实作用。但历史起作用,首先是她被尊重,开诚布公方可以立信。钱穆先生于抗战期间写《国史大纲》,以作国人应对时代种种事变的借鉴。在长达十五节的“引论”部分,他说出在国民中间传播历史知识,其中的关键是:“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,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。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,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。”
深厚的认识,真实的了解,这正是我们所主张的对历史的一种态度。
推荐「看历史」三月号「抵抗失忆」。虽然在一月份国家记忆•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上,听他们讲过,但读齐邦媛、野夫、孙春龙等人的文章,感受他们的感受,忍不住泪眼迷离。他们站在我们身后,仰望星空,回望来路,温故以知新,鉴往而知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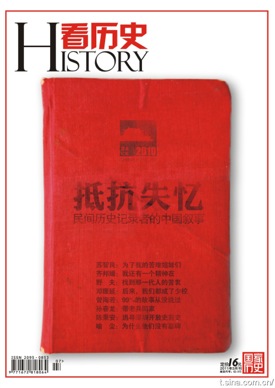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